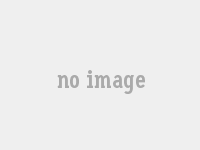纪念碑是人类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通常,它是碑体建筑、雕塑、绘画、文字、相关环境规划、灯光、绿化等要素构成的综合体,但基本上可以定位于一个建筑构筑体。雕塑在纪念碑综合体中具有着最重要的地位,即使是没有采用纪念性浮雕或圆雕的纪念碑,其碑身造型,也可以视为一个抽象雕塑的形体。世界各国与各民族,无论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有何区不同,对于凝聚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纪念碑建筑与雕塑,都是十分重视的,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与物力。而一座建立在大城市的重要纪念碑,其观众可以轻易地超过数百万人,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仅就观众人数这一因素而言,纪念碑及其雕塑是最具有公共性的艺术类型。新中国建立后培养的第一代雕塑家,主要是从事纪念碑雕塑的,直到1970年代,纪念碑雕塑及纪念性雕塑始终是新中国雕塑的主流。目前在中国的土地上矗立有多少纪念碑及具有纪念碑性的雕塑,尚无确切统计,但它确实已构成了我们的文化生存环境,成为现代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份,对纪念碑从历史、文化、建筑、雕塑、伦理等专业角度加以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也可以了解一个时代的雕塑艺术的发展脉络。本文对纪念碑及其雕塑从建筑艺术的公共性角度加以研究,试图为中国当代雕塑对纪念碑建筑与雕塑的借鉴和发展,提供一个艺术史研究的新视角。
一、纪念性建筑的伦理功能
在讨论纪念碑之前,我们有必要研究作为公共空间中的建筑或具有纪念性的建筑所内含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建筑的公共性。建筑对于人类,除了其所必备的实用功能之外,最重要的在于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和《筑、居、思》两篇论文中十分重视“栖居”(Wohnen)的概念,正是因为它比较贴近“存在”之意。他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一文中,称希腊神殿“作为艺术作品开启了一个世界,同时又反置这一世界于土地”,作为具有纪念性的神殿,它“首次把各种生命及其关联方式聚拢起来,合成一体,在这潜在的关联中,生死、祸福、荣辱等,俱以命运的形态展现在人类面前。而这一关联体系包容的范围,即是这一历史民族的世界。”【1】建筑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人通过与建筑的亲在接触,才获得了生存的经验与存在的意义。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卡斯滕•哈里斯在《建筑的伦理功能》一书中讨论到建筑的公共性问题,他认为“宗教的和公共的建筑给社会提供了一个或多个中心。每个人通过把他们的住处与那个中心相联系,获得他们在历史中及社会中的位置感。”【2】哈里斯所使用的“伦理的(ethcal)”一词,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ethics(伦理、道德)”,而是与希腊语中的 ethos(精神特质)相关,“建筑的伦理功能”就是指它帮助形成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任务。这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可以称之为对神圣、崇高等精神价值的信仰。人们正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信仰,从传统价值观中汲取必要的力量。当海德格尔在谈到希腊神殿时,与我们在具有纪念碑性的公共性建筑面前所感到的那种共享的东西是一样的。建筑的精神功能,就在于“它把我们从日常的平凡中召唤出来,使我们回想起那种支配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的价值观;它召唤我们向往一个更好的、有点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3】为什么一个民族要在最为重要的地点如城市中心广场为死者留出空间?“纪念碑”(monument)一词源于拉丁文monumentum,本意是“提醒”和“告诫”,还有“建议”、“指示”之意。它可以是一座碑,也可以是一个雕像、一个柱子,一座建筑。也就是说,有许多雕塑也许没有安放在广场,也没有与建筑物结合在一起,但由于它所具有纪念性内涵,从而具有了“纪念碑性”。同样,一所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无论它是官方建筑或是民居,只要它具有对民族历史与文化具有价值,也具有“纪念碑性”。“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在《新威伯斯特国际词典》中定义为“纪念的状态和内涵”,它不仅有巨大的、持久的、艺术中的超常尺寸的含义,也指在历史中那些显著的、重要的、持续的价值。例如,在2003年春中国的“抗非典”斗争中,为了纪念那些为国为民牺牲的医生、护士,北京、广东等地的雕塑家为这些平民英雄创作了肖像雕塑,这些雕塑都可以视为纪念英雄的纪念碑。面对城市广场中的纪念碑和各种纪念性雕塑和建筑,市民不仅会想起自己的祖先,也想到先他而去的几代人,想到民族的杰出人物,想到那些为了祖国而战斗并牺牲的英雄们。“铭刻碑文的纪念柱给死者以荣誉,令生者不仅记住了牺牲了的英雄,而且直面自己永存的死亡的可能性。面临那种可能性,他们会问他们是谁;通过思忖牺牲了的英雄的生命意义来度测他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不只是记住英雄,生者还应把他当作榜样,继承他的遗志——使自己被死亡束缚的生命隶属于城市的生命。”【4】
东南大学建筑系的童寯教授,对纪念性建筑有一个概括的诠释:“纪念建筑,……顾名思义,其使命是联系历史上某人某事,把消息传到群众,俾使铭刻于心,永矢勿忘;……以尽人皆知的语言,打通民族国界局限;用冥顽不灵金石,取得动人的情感效果,把材料与精神功能的要求结为一体。”【5】
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柯布西耶认为:“建筑这一行就是要利用未处理过的材料,建立感情上的联系。”【6】由于纪念性建筑的功能要求,“这类建筑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的‘表情’(建筑的形式、体积、质感、光影、空间、环境……)要能够唤起(或保持)人们的思念、回顾、敬仰和膜拜心境的持续性。因此,它们的建筑图像语汇一向被人们认为应该是既富个性、严肃性,又要具有文化脉络和超常的尺度。”【7】在这里,建筑的表情或建筑的意味(相对于诗意而言,也可称之为“建筑意”)成为建筑上升为艺术的决定性原则。象柯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那样,建筑通过发挥其超越日常实用功能的精神性功能,成为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圣殿。纪念性建筑的文化脉络与超常尺度,成为历史维度与现实空间维度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前提。
二、建筑、雕塑作为纪念碑的公共性
讨论纪念碑的公共性,在于纪念碑对于世界各民族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功能。
在建筑史家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的《建筑类型历史》一书中,将民族纪念碑及天才人物纪念碑作为首先论述的建筑型式。对于大部分西方人来说,建筑史始于金字塔及纪念碑式的陵墓。作为公共建筑的纪念碑,它的公共性体现在哪里?从建筑的哲学与精神意义上来说,陵墓与纪念碑以及纪念碑性的建筑使我们注意到本质的东西,即我们只有一次的被死亡束缚的生命。德国建筑理论家鲁斯(Adolf Loos)从“艺术不具有实用的功能”出发,认为真正的艺术使我们回想起海德格尔称作真实性的东西,这种真实性使我们离开日常的现实,认识自我并让我们回到真实的自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不无夸张地认为建筑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份属于艺术,即陵墓与纪念碑。【8】在世俗的、社会的意义上,为死者建造的纪念性建筑物,不仅是为死者的,更多地是为了满足活着的人(尤其是有权力的人)的需要。就金字塔、凯旋门、纪功柱、先贤祠、纪念堂、秦始皇陵、武则天墓这些纪念性建筑物来说,它们的构筑耗费了大量的集体劳动,通过给予那些为它建造基础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以荣誉的方式,为统治者提供了表现他们统治权的合法化证明,通过承诺过去所建立的不会成为时间流逝的牺牲品来帮助维护统治权。通常,陵墓与纪念碑也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场所,一个祭坛,它将公众召集到它的周围,看似召集到一种神与命运的周围,实际上就是召集到建筑与掌管它的统治力量的周围,通过仪式的举行,在宗教与世俗的不同层面上,使公众以陵墓与纪念碑为中心,形成民族的、社会的、城市的或集团的精神、文化向心力,强化某一时代的思想、信仰与价值观。所以,一座纪念碑或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是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些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秦时明月汉时关”,在这里,陵墓与纪念碑以及所有具有类似功能的纪念碑性的建筑物,成为某一社会共同体世代相传的精神纽带,成为人类永恒的精神中介物,以及沟通生死两界、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桥梁。作为仪式场所和祭坛的建筑物,是一种象征的符号,它最大的艺术功能就是精神意义的生成,以其崇高和理想的价值召唤与公众进行心灵的对话沟通,正如赫伯特•里德所说:“艺术总是一种象征性的对话,一旦没有象征,也就没有了对话,也就没有艺术。”【9】
另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是,雕塑特别是处在公共空间中的雕塑,更具有艺术的非实用性,它们在传统中也具有纪念碑性质。罗沙林•克劳斯在《后现代主义雕塑新体验、新诺言》一文中写道:“雕塑在传统上被看作在纪念碑的逻辑中。作为某个祭典场地的标志,它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它的形式是具象的(不是人就是动物)或抽象的、象征的。就其功能的逻辑而言,一般要求它能独立于环境,要有垂直于大地的底座,易于辨识。作为一种实在,有许多雕塑作品能被人们毫不费劲地认出来,道出名字并举出其意义所在。”【10】通常,在纪念性建筑总体中,雕塑与建筑物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它们共同构筑了人类的精神生活空间,以其材料的永恒、形式的多样、内涵的深刻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明产生绵延不断的影响。
在人类的历史上,不同的文明、民族都修建了许多纪念碑性质的建筑或构筑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显示了纪念碑对于民族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例如,公元前3000年爱尔兰的通道陵墓与石阵就可以视为纪念碑性质的构筑物。【11】同样,在墨西哥玛雅文化的历史中,很早也产生了纪念碑,它们更多的与宗教祭祀有关。【12】
中国的纪念碑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就已使用了刻石记事的方法,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这样概括:“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逮及魏晋,屡申刻石之禁,至南朝而不改,隋唐承北朝之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记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刻石文字几遍全国矣。”【13】虽然汉代霍去病墓石雕是中国古代纪念碑性雕塑的经典,但中国古代纪念碑的全盛时期是唐代,从唐碑的巨大形体和精美浮雕可以想见大唐帝国的辉煌。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刻石真迹,是陕西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两个春秋时期的石鼓,被称之为石刻之祖(据说共有十个,今余9件)。每个石鼓上均刻有大篆文字,称之为“石鼓文”,此石鼓据记载在唐代发现于陈仓石鼓山(今陕西宝鸡石嘴头)。石鼓文是十首记述秦国君猎祭活动的四言诗,意在刻石表功,这是否可以视为一种碑石?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这些石鼓都可以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纪念碑。而秦代的《琅琊》、《泰山》两刻石,是秦7件刻石幸余的两件真品,记载秦始皇巡幸各地的情况,也充分体现了纪念碑所具有的刻石记事,传之久远的特征。
三、纪念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在1903年出版的《纪念碑的现代崇拜:它的性质和起源》一书中,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 Alois Riegl)认为纪念碑性不仅仅存在于“有意而为”的庆典式纪念建筑或雕塑中,所涵盖对象应当同时包括“无意而为”的东西(如遗址)以及任何具有“年代价值”的物件。
1980年马塞诸塞大学出版了美国学者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可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的《对于废墟的需求》一书,杰可逊注意到美国国内战争后出现的一种日渐高涨的要求,即希望将葛底斯堡战场宣布为“纪念碑”,这使他得出“纪念碑可以是任何形式”的结论。这一观点强调“类型学和物质体态不是断定纪念碑的主要因素;真正使一个物体成为一个纪念碑的是其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14】这是一种“泛纪念碑”的观念,它拓展了人们对“纪念碑性”的认识,但也使纪念碑的研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式与样式,从而突出了纪念碑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1992年华盛顿大学召开了一个以“纪念碑”为题目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纪念碑?它是否和尺度、权力、氛围、特定的时间性、持久、地点以及不朽观念有关?纪念碑的概念是跨越历史的,还是在现代时期有了变化或已被彻底改变?”会议的组织者试图建立起一种在交叉原则和多种方法论基础上来解释纪念碑现象的普遍理论。
艺术史研究不仅要描述一个历史时段总体上的艺术演变过程,同时也要发现某些偶然事件并确定它们对美术和建筑的影响。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认为,“纪念碑和纪念碑性的发展不是受目的论支配的一个先决历史过程,而是不断地受到偶然事件的影响。有时某一特殊社会集团的需求能够戏剧性地改变纪念碑的形式、功能及艺术创造的方向。”【15】以林缨设计的美国越南阵亡纪念碑为例,它的设计受到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和压力,不得不对原设计作出较大改变,它证实了艺术家对于处在公共空间中的雕塑艺术并没有画家对室内绘画那种绝对的支配权,许多室外公共艺术项目的完成是各种社会集团不断调整、改变与妥协的结果。【16】
对于艺术史研究而言,无论是纪念碑还是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最重要地是要把握“纪念碑的地位和意义体现于其具体形象中的特征如材质、形体、装饰和铭文”。我们研究现代纪念碑的建筑设计,要注意它与古代纪念碑不同的重大变化,如纪念碑的位置规划、形体高度、碑体主立面方向、浮雕内容、碑身形式、材质选用等。形象的分析与图像的阐释,应成为艺术史研究区别于一般历史研究的文献分析方法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应该将纪念碑与雕刻作为象征的图像进行研究,在这里,作品考察与图像分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挪威建筑理论家C•诺伯格•舒尔茨在《居住的概念》一书中认为,“建筑语言”包含形态学的、拓朴学的、类型学的三方面要素,并把这本书称之为“走向象征的建筑学”。清华大学汪坦教授认为,“象征”原文为Figurative,也可译为图形的,三个要素都是解释形象的属性。【17】在建筑史与雕塑史的研究中尽可能采用作品图片与历史照片,对图像的文化内涵和作品的形式风格进行分析,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史方法论的认识。
19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开始和更为深广的社会存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著名美术史家克拉克(T.J.Clark)就强调指出,应该把艺术史变成一种充分顾及艺术赖以生长的社会现实的历史。【18】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格斯伍德(Charles L. Griswold, Jr.)也指出:“为了对某些纪念碑所纪念事物的意义做反省,只从建筑理论的技术面或建筑物的历史来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了解纪念碑的象征意义、它所处的社会情境,以及它本身对前来观赏的人产生了什么影响等层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它由公众与舆论所形成的政治意象。”【19】也许我们应该持有一种更为宽泛的美术史观念。这种观念,从美术史的资源来看,注重资源的文化性,即不仅注重从艺术角度采集分析与艺术家、艺术作品相关的美术史资料,也从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角度收集与艺术相关的史料。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形态的历史资料,如研究文献、史籍传记、报刊杂志、公函通信、统计报表、会议记录、工程图纸等,都可以纳入一定的艺术史氛围中加以感受与观察,分析其史料遗存现状和可靠性。从方法论的角度来,不同于相对独立的架上绘画或室内雕塑,对于纪念碑这样综合了建筑、绘画、雕塑的大型公共艺术工程,应该将它们作为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加以辩证研究。它们必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得到观照分析和比较研究,除了传统美术史所重视的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有关纪念碑的传统文脉、纪念碑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纪念碑建筑与雕塑的关系、大型公共艺术项目的组织、管理、经济、技术等也应进入艺术史研究的视野。
注:
【1】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载《林中路》,法兰克福,1950年德文版第27-28页。转引自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8页。
【2】卡斯滕•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陈朝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79页。
【3】【4】同上,第284页,第289页。
【5】【7】转引自徐伯安《纪念性建筑》,《建筑史论文集》,第1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77页,第172页。
【6】【9】[美]史坦利•亚伯克隆比(Stanley Abercrombie)著、吴玉成译《建筑的艺术观》(Architecture as Art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33页,第129页。
【8】Adolf Loos . "Architektur" in Trotzdem, 1900-1930, Innsbruck : Brenner, 1931, p.107
【10】转引自《创作、理性、发展——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学术论文选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1999年9月第1版,第29页。
【11】 在爱尔兰境内,散布着1200多处纪念碑性质的构筑物,它们就是爱尔兰的先民们建造的巨大的石阵和被称为通道陵墓的人造丘冈。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爱尔兰进入石器时代,各部落开始建造通道陵墓,通常,在地面上架起三至七块立石、上面覆盖一块巨大的盖顶石(这与中国唐代的石碑结构颇为相似,只不过唐代石碑多有基座,并且形制更为精致),有点象庞大的石案陵墓用的石头有的重达100多吨,举起并安放这些石头,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巨大的力量,爱尔兰人将这些建筑归功于神灵之助。在爱尔兰的纽格林治,有一个欧洲最大的通道陵墓,用重达4000多吨的石块建成,覆以泥土,一部份有围边石和较小的石英石围绕。每年冬至日的早晨,阳光从通道陵墓上方的特别开口射进墓道,穿过其中的一个墓室。根据爱尔兰的神话,此世与彼世通过湖泊、山洞和通道陵墓可以交通。参见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出版,李绍明译《祭司与王制:凯尔特人的爱尔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1页。
【12】从奥梅克时代开始,美索亚美利加文明的艺术传统就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宗教题材的繁缛庄重,主要表现在纪念碑和建筑雕塑上,另一种是具有儿童般天真与质朴的民间艺术。在玛雅文明的前古典期(公元前1800年—公元250年),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通常是与建筑物联系在一起的建筑纪念物,并不孤立存在。在莫雷洛斯州霍奇卡尔科“A”结构的供品室出土的三号碑(现藏于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上,我们可以看到石碑表现了奎扎科特尔神在一种自我牺牲仪式上的痛苦表情,石碑上部的“四方运转”图案和下部排成一列的心脏使典礼仪式的情景表现的更加突出。这种传统延续到古典期(公元250—900年),在墨西哥瓦哈卡州仍然有雕有人像的石碑(现藏于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出土。以上资料来源于《墨西哥玛雅文明展览》,北京,中华世纪坛,2001年7月27日。
【13】梁山鸣《我国碑刻的发展及两个高潮的出现》,天津,《中国书画报》,1987年8月15日。
【14】Wu Hung.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
【15】同上, p.13.
【16】越战结束后,为纪念阵亡将士,1984年,由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会公开征集方案,委托建筑师、景观规划师、艺术评论家和雕塑家组成8人评审小组。共有1421人报名参与送图,是美国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竞赛。最后由当时尚在耶鲁大学建筑系就读的林樱(Maya Lin)获得首奖。这一设计突出了极少主义的美学特色,由纯黑磨光的花岗石建成的V型纪念碑,各250英尺长,以125度分叉指向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按照字母顺序刻列57,939位阵亡将士姓名。获选名单及设计公布后立即纷扰不断,反对的意见有“抽象几何的造型无法代表阵亡军魂”,有“黑色岩石有种族歧视的暗示”等,后来退伍军人分为两大阵营,由艺术界支持林樱,对抗另一方由德州财阀支持的保守势力。最后由一位黑人将军出面调和争议,保留林樱的原方案,另外增加一件哈特(Frederick Hart)的青铜雕塑置于升旗台附近。岁月流逝,当年的争执已化为云烟,哈特过分细节化的黑、白、棕三位不同人种的军人雕像,并未吸引广大观众的注目。相反,当时倍受攻击的林樱的设计,吸引了无数的观光游客和阵亡者家属与友人,他们在如镜的石面上抚摸寻找自己的亲友姓名,或对着自己依稀的影像默想生命的意义,反思战争的残酷,或献上鲜花,或在纸条上磨印出拓痕带回家作为纪念。请参见陆蓉之《公共艺术的方位》,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4页。
【17】转引自林洙著《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26—127页。
【18】丁宁《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97年8月第1版,第53页。
【19】Harriet F. Senie & Sally Webster Critical issues in public art: content, context,and controversy ,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1999, p.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