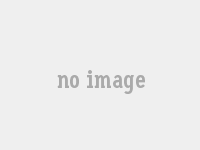近日,《遭逢美杜萨》(Encounter Medusa)艺术展览于上海巽汇艺术空间举行了开幕式,并展开了一场围绕“人与非人之身”的会谈。此次展览由学者寒碧、孙周兴任总策划,汉学家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为策展人,北京大学戴锦华任展览学术主持,艺术家、艺术史学家严善錞为展览总监。展览将持续至11月10日结束。展览主题“遭逢美杜萨”为策展人阿克曼所定,展品包括两件作品,靳卫红的纸本作品《疼痛》(Pain)和向京的雕塑作品《降临》(Descending)。两件作品放置于同一个空间中,构成了一个整体。
作者也没有权力去定义作品?
《疼痛》是一幅水墨画,占据一整面墙之余,底部还拖出来一小截。画的内容是女性生产,胎儿滑出母体的瞬间。靳卫红说,这幅画的创作是一气呵成。借由这幅作品,她想表达的“疼痛”,不仅仅是一种感觉上的不适,更是一种剥开直面的态度。在日常生活里,疼痛是一种被忽略、不被提及的感觉;一个屏幕挡着的社会,人们会展示快乐、幸福、甜蜜、美好,不会轻易地展示疼痛,但是它无处不在。

从五官四肢的汗水到抽搐蜷缩的脚趾,连带着母体的“疼痛”都跟着被放大。《疼痛》(局部),靳卫红。靳卫红供图。
直面于仓惶、惨淡、狼狈的人生,是中国艺术史里很少发生的。佛教绘画中释伽牟尼对人世的参悟,虽是以痛苦作为基础,但表现得还是相当克制。靳卫红想要把人的不堪、无力、狼狈捧到观者面前,刺激人的知觉力,以幽微来对抗喧嚣的历史洪流。
《降临》由硅胶制成,构型是一只吊挂着的大章鱼。在开幕式上,策划人孙周兴表示,从章鱼的物种特性出发,《降临》有一种解读是死亡的冲动与性的本能。再者,章鱼触须的造型,似乎和美杜萨的蛇发也有些形似。

《降临》,向京。向京工作室供图。
向京不喜欢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太多阐释,她认为作者也没有权力去定义作品。在她看来,人和人之间可共情的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艺术作为可感物到底是情感化的、情绪性的,还是思绪的、观念的,这个判断权应该留给观者。《降临》作为一个理解的通道,基于作品会得出什么样的阐释全在于观者。
《疼痛》与《降临》,引发有关于“身体”的思考
在对谈现场,针对两件作品所构成的整体,戴锦华详谈了自己的视角和解读:《疼痛》表现的是母体生育,从产道里滑出的胎儿,其中表现的冒犯和熟悉,似乎有一种更强的指向:这是一个女性主义展览,这是女性艺术家关于性别遭遇的表达。如果单独去看《降临》,多义性也许会更强,但和《疼痛》放在一起,解读似乎也受到了局限。

对谈现场,从左往右依次为寒碧、廖雯、靳卫红、向京和戴锦华。巽汇XUNWAY供图。
戴锦华说,若进一步思考《疼痛》的表达方式,水墨作画,中国的传统水墨画背后是文人,文人的指向其实是男性。男性、女性、两性世界等都是西方的概念,到中国不过一百年。在这些西方概念到来并渗透进我们的文化之前,中国传统的男性文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放诸女性形象之中,借助某种女性生命经验来传达自己的社会经验。但是,这种穿行结构并不同样适用于前现代和现代的女性,女性穿越到男性的君臣关系之中的方式需要化装成男性,比如花木兰。
《疼痛》的呈现是女艺术家在男性文人形成的介质和语言系统中,试图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放进去,却没有选择花木兰的方式,这种生命经验必然是撕裂的。这也是《疼痛》会给观者带来一种不适感的原因所在。
《降临》所用的雕塑介质与这些介质对语言的改写是非常物质化、非常具象的,就像挣脱而出的灵魂,作品的背后是宁静与宁静中的嘶喊与不安。在作品背后含义的表达层面,两件作品似乎有一种统一与协调,《疼痛》强烈挣扎背后的不适,《降临》宁静背后的不安。
戴锦华提示观者不要被展览中的性别元素所限定。向京的《降临》与靳卫红的《疼痛》相遇,其意味不仅在于性别,更在于身体,某种在新技术革命击毁之际的身体陈述与反思。身体,事实上成了人类主义或曰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固守的最后基地与仅有依凭。
艺术可以唤醒我们身体中的经验
展览的名称“遭逢美杜萨”,来自希腊神话美杜萨的故事。阿克曼说,“古希腊文化的一大天赋在于能将人类的‘神遇’经历浇铸成故事的形态。也正因此,这些故事如今依旧在被讲述,不显老套,不失魅力。”
美杜萨的故事有许多版本,解读也是多重的。其中有一个版本,讲的是海神波塞冬将美杜萨诱骗至雅典娜神庙,强暴了她。雅典娜将美杜萨的头发变成毒蛇以作惩罚,蛇发女妖美杜萨一个目光便可将人瞬间石化。英雄珀尔修斯割下美杜萨的头,将它献给雅典娜,这颗头颅从此成为了雅典娜神盾上的点缀。
基于这个故事版本,阿克曼选定美杜萨为展览主题。他给出了三点阐释:美杜萨是女性吸引力的牺牲品、男性暴力欲望和道德义愤的受害者;“神遇”有致命的危险,同时也是不可抗拒的;美杜萨代表了神性的两面:极端的美和极端的可怖。他反复强调,取名“美杜萨”,关注的不是美杜萨本身,而是神的双面性:极端的美和极端的可怕,极端的、超越的经验。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策展人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巽汇XUNWAY供图。
阿克曼强调,无论在主题、媒介、技术、材料上,还是在形式上,《降临》与《疼痛》都大相径庭,但两者都重述了“神遇”的经验。两件作品都反映了不可抗拒、欲望、恐怖、诱惑和疼痛的经验,她们从自身“甩出”了作品。两个大不同的作品,被放入同一个空间,创造了一个整体。
从艺术作品出发,阿克曼关注的是当下现实的生活。在如今的发展态势下,权力、政治、经济、技术、哲学、科学和医学系统都在规避“神遇”的经验,这些系统都承诺“人类动物园”的永生和恒久幸福。它们是无法控制对人的诱惑,是从分娩、情欲、疼痛和死亡的恐惧感中衍生出来的产品。
阿克曼认为,系统性白痴化许诺的是一个安稳的人生,但前提是我们甘于沦为被大数据能够计算的消费者,美杜萨的威力正在消逝。艺术并不一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阿克曼相信,艺术可以唤醒我们身体中的经验,这些经验增强了对抗系统性白痴化的免疫力:“当艺术有勇气一步步靠近美杜萨的头颅,直视她的眼睛,便有了唤起这些经验的力量,这就是‘神遇’。若艺术能够赋予神性以适当的形式,便能召唤它的‘降临’。”
阿克曼说,与以往的艺术不同,神学和美学规则无法再为艺术家提供帮助,当代理论或概念也不能够取代形而上学的经验。靳卫红和向京的两件作品,有意识地离开了“传统”与“现代”的保护区,完全暴露在超验之中,将这样的经验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语言。这里的“疼痛”不是药物能克服的疼痛,“诱惑”也不是约会配对的APP满足性欲的诱惑,而是超越系统的“神遇”经验——具有神性的残酷、压倒性的疼痛和诱惑。
《疼痛》与《降临》的融合让阿克曼看到了“神遇”,从身体上感受到的“疼痛”与“诱惑”到经验与超越经验之上的感知。被现实生活剥夺的感知力能否通过直视艺术召唤回来,是《遭逢美杜萨》希望能够得到积极回应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