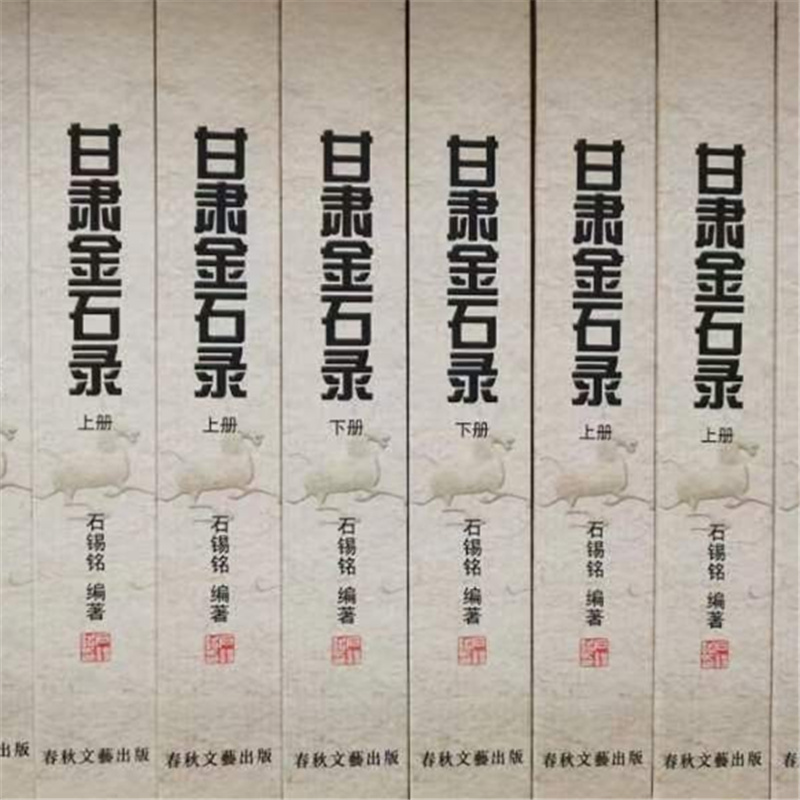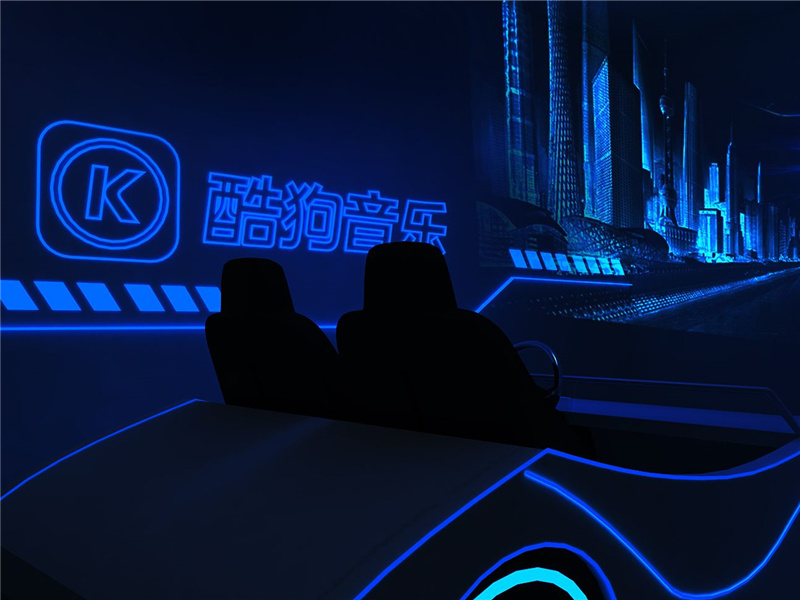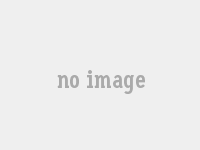托马斯·品钦的长篇小说历来以难读难译著称,《葡萄园》发表于1990年,国内已出版的只有张文宇先生的译本,共两个版本(译林出版社,2000年9月,平装;译林出版社,2018年5月,精装),相隔十八年。我读的是精装再版,一读吓一跳,后来想起“十八年”,被迫理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本书的再版修订用的滤网口径比较大,才会放任那些音乐名词翻译上的纰漏与草率。
新版的托马斯·品钦《葡萄园》
这种感觉从第六页开始。译者将“New Age music”翻成“新时代音乐”(华语地区通译“新世纪音乐”,港台地区还有“新纪元音乐”的别称)。这很别扭,相关译注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末期流行的一种音乐,糅合了爵士乐和传统音乐主题,用各种电子合成器或其他同类高科技乐器演奏。”作为一个资深乐迷,我对“爵士乐”的硬闯表示质疑,“传统音乐”不妨改成“民族音乐”。
也许是我吹毛求疵,但在书的勒口,作者介绍的下面,译者简历的末尾,我见到了“通音乐”三个字。
再看145页:“自动唱机里放着‘门’、‘吉米·亨德利克斯’、‘杰菲逊飞机’、‘乡下佬乔’和‘鱼’。”译注写道:“此处及以下均为摇滚乐著名演出组合或歌星。”如果说“门”的出现让我们想起The Doors(大门乐队),是别扭的延续,那么把迷幻摇滚(是的,品钦这一列的四个名字都很大牌,都是1960年代出道,都为乐迷制造迷幻)名团Country Joe and the Fish拆成“乡下佬乔”和“鱼”两支乐队就有点过分了。
迷幻摇滚名团Country Joe and the Fish被拆成“乡下佬乔”和“鱼”两支乐队
英文原文截图
在328页,译者为Willie Nelson加注,加得认真到位,似乎还不过瘾,于是,画蛇添足:“与朱里奥·伊格利谢斯合作过歌曲《献给所有我爱过的姑娘》。”我想为译者说一句好话,他有服务读者的热情,这是一种优良品质,只可惜,西班牙歌王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Julio lglesias)的名字并不适合按照英语来翻。就此,我有两点疑惑,译者为什么要追加一句?他今年几岁?我想起在1980年代初之前出生的欧美音乐听众,似乎都知道卡朋特乐队、猫王、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那似乎是烂大街的名字。
“通音乐”的疆土不包含摇滚和流行两大洲,然后是爵士。
359页:“听伯德、麦尔斯、迪济和当时在海岸的任何人物的节目,在低矮的金属天花板下,和跳波普舞的、抽大麻烟的、长山羊胡的、戴馅饼式男帽的挤在一起。”看到“伯德、麦尔斯、迪济”,爵士乐迷可以起立了——Charlie Parker、Miles Davis、Dizzy Gillespie,爵士乐史的三座丰碑——正如中国人见到“凌冲、宋姜、花融”,脑海里也能“大河向东流”。问题是译注。译者简直是在演义:“麦尔斯·戴维斯(1926-197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伴舞乐队指挥。”我被这条译注搞得哭笑不得——麦尔斯·戴维斯少活了整整二十年,还有,伴舞乐队指挥是什么鬼,大概是Bandleader,但是爵士乐团(Band)的领队和爵士大乐队(Big Band)的指挥区别还是蛮大的,指挥那是Bandmaster。
离奇的麦尔斯·戴维斯注
翻阅原文,我更迷惑了,“and listening to Bird,Miles,Dizzy,and everybody else then on the Coast,under the low metal ceiling among all the boppers,reefers,goatees,and porkpie hats”,译者如果真是爵士外行,何以通过三个似是而非的名字就能缉捕到Miles Davis?还有两处需要提醒读者:1)on the Coast出现了大写,我猜作者是在特指,比如某酒吧的名字(上下文未见),或者爵士乐的某种流派,该流派和Bird、Miles、Dizzy有某种瓜葛,我听爵士乐还比较浅,不敢轻下结论,答案也许是West Coast jazz,但不应该被翻译成:“听伯德、麦尔斯、迪济和当时在海岸的任何人物的节目……”2)Boppers不是“跳波普舞的”,而是指女性为主的青年乐迷。
英文原文
其他的音乐问题,如344页,Pink Floyd翻成“平克·弗劳埃德”;391页,Motown翻成“汽车城音乐”——应是摩城之声,或者摩城唱片。类似情况还有,无需再列举,但值得展开,因为这是国内音乐书籍在译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我觉得译者处理这类图书,可以强行将人名、专辑名、歌名以及相关的名词译成汉字,但应该保留原文,或在正文加括号出现,或挪至译注。
前阵子我读了上海音乐出版社今年的一套重点丛书,引进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为英国Phaidon出版社主编的那套“二十世纪作曲家系列”。这套佳作十几年前我在福州路外文书店见过全套原版,买了一本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英语不好,读得很潦草。后来听说“上音”敲定了版权,请内行在译,一直很期待。事隔多年,说实话,这套书的译本和装帧还算可以,印数三千,收藏和品读俱佳,只是《爵士豪杰》(Jazz Greats)那本有些瑕疵。
《爵士豪杰》
一本品鉴音乐的书必须为读者提供方便,可第九页,“爵士缘起”那章,当我读到:“在新奥尔良街头,第一次响起的令人兴奋的爵士之声是一位名叫‘彼得·波卡基’的小号手奏响的……”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出过唱片吗?我想听一下。没有原文,我需要翻到239页以后,索引里有人名对应表。姓“波卡基”,那应该是字母B开头。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不禁要问。这本书的译注还特别少,两百五十多页的“爵士列传”,只有八条译注(严格来说是七条,135页和194页,译者对Ghetto“隔都”的解释重复出现)。作为一种流行曲风的Tin Pan Alley其实应该加注展开,Minstrel Show也是,估计多数乐迷并不清楚“墨面秀”对美国音乐剧发展的突出贡献。还有一点也许是遗传疾病。书中28、29页的照片,Buddy Bolden(据说是第一个演奏爵士乐的人)的乐队,这张照片非常著名,在Jazz的维基页面就能看到,却被印反了,图注也有问题,拍摄时间大约在1905年,而非1900年。
维基百科上Buddy Bolden乐队的照片
书中乐队的照片被印反了
同样是这套书系的《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就好许多,译者刁康宇加了194条译注。我不是鼓励疯狂加注,比如迈克尔·杰克逊是否注解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回答的问题。我想表达的是,与其责备《爵士豪杰》的译者失职,还不如说他缺乏热情。我想起李健吾先生翻的《包法利夫人》,我最早读福楼拜就是通过他的译本,也有问题(吐槽可见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6月,P152-153),但是李先生对待译注的钻研态度让人心悦诚服,那可是查阅不便、资料匮乏的特殊年代。
《本杰明·布里顿》
李健吾为《包法利夫人》加的部分译注
还是回到《葡萄园》。那些被译者曲解的音乐世界也许比读者想的要巨大,它们是品钦文学的重要组成,刻画人物,营造气氛,甚至透露一些弦外之音。231页:“他们最后还是安全过了桥,把所有的夜行灯都打开,咔一声把伯纳德·赫尔曼的盒带塞进去,车子在《变态》的音乐的伴奏下,沿影溪谷公路驶向前去。他们最后找到了果园,并借助聚光灯找到了树顶上的一辆丰田车……”在这里,互文出现了,品钦借用了希区柯克经典电影《惊魂记》(Psycho)的配乐,甚至是一些影像桥段。我们现在提起作曲家伯纳德·赫尔曼(Bernard Herrmann)总不离开他的那些电影音乐,尤其是用提琴来抽观众神经的《惊魂记》主题曲。诸位不妨重温一下这段音乐,脑补一番品钦笔下深夜疾驰的场面,是否有一点变态?我翻阅了品钦的原文,Psycho是斜体的,后面有被译者删掉的“(1960)”。他似乎在强调什么,向读者传递着什么。
《惊魂记》被译成了《变态》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