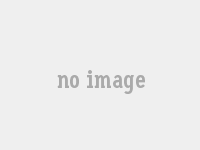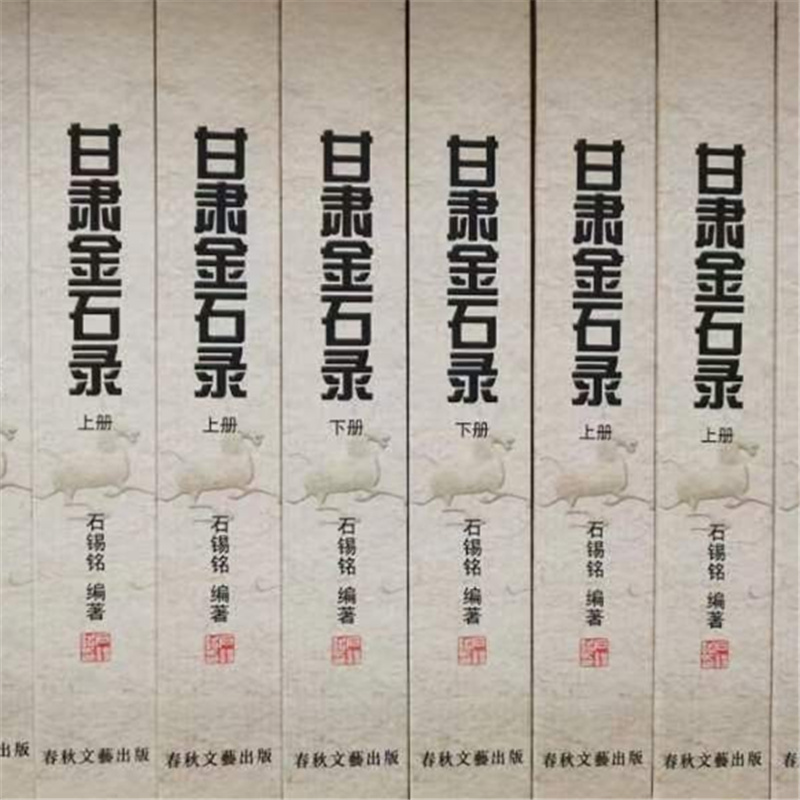从山西许村到广东青田村,路程不足2000公里,但是从“许村计划”到“青田范式”这条乡建之路,渠岩走了十年。乡建二字,知易行难。 许村和青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乡村样本,一北一南、一山一水,借鉴许村的经验,并经过两年的调研后,2017年,渠岩确立了两种模型:许村是从“艺术”入手,寻找传统文明的原码;青田隐去“艺术”之痕,构建中华文明的现场。在渠岩看来,处理许村艺术乡建正确的关系是相互尊重与认可、互为他者,建构新的乡村共同体。“澎湃新闻·艺术评论”本期推出的艺术与乡建系列关注一些艺术家在乡村的实践。本文由《中国艺术》授权刊发。 1908年,留学回国的米迪刚在自己的家乡河北定县翟城村建立乡村合作社,实行村民自治,并率先提出“农村立国”的理念,推开了中国乡建的大门。及至“乡建先驱”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到“新农村建设”,乡建已经踉踉跄跄走过了110年。 将渠岩以个案方式来呈现,既是因为他完成并践行了两种乡建模型,而这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样本于当下具有典型代表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实践中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渠岩以共生的路径,在村民、商业等多种关系网中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发展,他在许村的艺术实践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包括他们之前对于乡村的“绝望”与“期望”。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许村(摄影:文天平)两种乡建欲重建文明渠岩最初的研究领域并非乡建,学习绘画的他经历“85思潮”后,在布拉格亲历了东欧剧变,瓦斯拉夫·哈维尔、伊凡·克里玛、赫拉伯尔等东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于他产生巨大影响。2000年后的中国艺术界让刚回国的渠岩很不适应,资本的裹挟让艺术失去了介入现实的能力,他毅然背上相机去了中国最真实的现场——乡村。这场采风之旅意外开启了渠岩的乡建之路。 在渠岩刚刚进行乡建实践时,还鲜有人关注乡村,将沉寂近百年的乡建再度拉入公众视野的,则是2014年一场风靡于网络的“辩论”。2014年,于哈佛攻读社会学博士的周韵跟着国际暑期班到安徽省黟县碧山村,实地探访后,她在《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一文中提出了多个疑问,其中一项剑指村里的路灯:村里人想要路灯,而外来人更想要看星星。路灯和星星的对决看似区区小事,实则知微见著,引出了问题的关键:谁的乡村?这个问题曾经也困扰着渠岩,在无数次深入乡村的探究中,并在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后,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核心——在以乡村为主体的前提下,恢复或重建乡村文明,以此来建设乡村。
《中国艺术》2018年第9期杂志十九大报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提到,必须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保留乡村特色风貌。十年来,渠岩在许村的乡建正是以保留乡村特色风貌为前提,他将其归结为主体性前提。“许村艺术乡建的主体就是村民。”对于主体性的问题,渠岩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认为,现在乡村的问题是过度现代化产生的问题,这就不能以精英主义居高临下的方式进行“现代化的抢救和治理”,比如“我赋予”“我要改造”等现代话语。从社会学和人类学来讲,正确的关系是相互尊重与认可,互为他者,建构新的乡村共同体。 如果说许村的乡建是一次偶然,青田村则是一种必然。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的许村位于太行山深处,属于全国贫困县,在这里做乡建可谓白手起家;地处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青田村,普通得几乎没有人关注,它在南粤纵横交错的水网里享受着现代化的红利,却在城市化裹挟中幸免于难。建设许村十年,并通过艺术介入让其蜚声海内外的时候,渠岩又只身来到了岭南水乡青田村。 许村和青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乡村样本,一北一南、一山一水,借鉴许村的经验,并经过两年的调研后,2017年,渠岩确立了两种模型:许村是从“艺术”入手,寻找传统文明的原码;青田隐去“艺术”之痕,构建中华文明的现场。 乡村作为尚未被完全开放的“纯天然蛋糕”,在城市化进程中,严重外流的人口以及不断推翻重建的房屋,各类开发者拿着“改造”乡村的刀叉,迫不及地瓜分每一口奶油。乡村产业化经济发展与致富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驱动力,乡村旅游、艺术小镇、艺术村落、有机农业、乡村文创、农家乐升级的乡村客栈,建筑师也不甘落后,在乡村积极完成自我表现的建筑作品。这些外部的介入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倾向。在许村十年的“行动之诗”,带给渠岩深深的感触:今日乡村的出路如果只是一边倒的产业化经济诉求,那就会离乡村的精神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精神家园也越来越远,更会加重中国文化的危机。 “谁的乡村,谁的主体,这是现在特别要强调的。但是也不能完全以乡村为主体,因为现在乡村村民的主体价值已经崩溃了,沾满了现代化的毒素,会用物质来判断你所帮助的价值。重建乡村的关系,是要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角色。”渠岩正是在妥协中完成了这种共建。通过主体性的确立,渠岩建立了一个艺术和乡村能够持续发酵、成长和发展的体系。
自清末起建造的房屋分布在水乡青田村荷花塘沿岸,浸染着南方的潮湿,以及乡村人口流失导致的屋去人空,均加速了建筑的老化。(摄影:陈碧云)许村十年确立主体性新世纪后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渠岩背着相机第一次进入许村。此行最初的目的是拍摄其声名在外的摄影系列“人间三部曲”,没想到自此开启了“许村故事”。“许村故事”萌芽于寒冷的冬天,却在温暖的夏天启幕。 许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其位于晋国与鲁国相接之处,村南边的夫子岭至今还流传着孔子“倒翻坡”的故事。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自2005年起,渠岩选择在夏天举办“许村艺术节”来激活这个日渐凋敝的乡村,他为许村制定了“许村计划”,包括“许村宣言”“许村艺术公社”“许村论坛”等,至今,两年一届的“许村艺术节”已经成为许村的“招牌”。在凉爽宜人的深山中,海内外友人集聚在许村,一边采风一边与村民交流,带来新的知识、思想以及技能。许村通过艺术和节庆,让乡村、社区和地方发展发生了有效的化学反应。现今,许村从“隐居”于太行山的小乡村,变为国际知名的艺术乡村。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摄影:王笑飞)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前任院长保罗·赫胥黎是影响英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三个人之一,在参加2011年第一届许村艺术节时,他不禁感慨万千:这才是中国,北京、上海是山寨的纽约、东京。西方艺术家在许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中国艺术家也在许村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现场。 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这似乎并不是艺术家的工作,却是村民的愿望,这就变成艺术乡建的隐性条件。就像此前路灯和星星的问题,两者是共生的,难以割裂。许村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农民想致富却找不到任何途径,许村艺术节为发展农家乐经济创造了条件。此前,许村有20多户农家乐,生意也不大好,现在不仅多出一倍,还多了一些饭店和商店,实现了许村人热盼的农家乐经济。让农民生活好起来,这正是艺术乡建为村民递交的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单。艺术家和村民一起走过令人难忘的岁月,见证了从凋敝到复活的乡村。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内景(摄影:王笑飞)从“艺术”入手,仅仅是乡建的一种途径,解决乡村的实际问题才是建设的根本。如何让艺术在乡村生效,这个问题困扰了渠岩多年。无数次进入许村,与村民同住、同吃、同建,当村里人把渠岩看成了自家人时,双方才渐渐进入了一种共生状态,乡建的作用才真正得以发挥。 艺术家为许村解决了什么?两年一届的艺术节、建立了许村艺术公社、村子里爱画画的聋哑人王仲祥的作品都有了销路、农家院的生意越来越好……更为实在的是,经过渠岩的多方走动游说,每次一下雨就坑坑洼洼的泥地不见了,村子里第一次有了下水系统。 许村为艺术家解决了什么?渠岩通过许村搭建了一个平台,让更多艺术家获得亲历乡村现场的机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重新构建了一种乡村应该存有的文化逻辑,解决了关于主体性的疑问。通过十年时间完成“许村实践”后,渠岩选择以乡村显性文化价值的载体——祠堂作为自己的作品,并用当代的手法进行再造。
许村艺术图书馆(摄影:王笑飞)只言片语的描述,不免让人觉得乡建不过就是一场节庆,实际上,看似轻松的背后带着各种现实难题。已经被村民视为“村里人”的渠岩也遇到不少“闹心事儿”。某一年春天,渠岩再次回到许村时,他意外地发现村子里那些饱经岁月浸透的老街古巷,墙面被一律刷成了白色。渠岩顿时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他苦心经营多年并声名远播的许村,只是一时的不留神,立刻被“穿衣戴帽”的新农村美化工程裹挟。把墙刷白这件事儿是中国每个村子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许村,这就与渠岩最初规划的“在不破坏乡村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乡村”的初衷相悖,崭新的白墙让他看到了一种并不高级的现代化在冲击着许村。“以前墙很好看,色彩斑斓,学生很爱来写生。现在墙都刷白了,学生不来写生画画了,摄影的也不来采风了,农家院就没有人住了,直接影响了村民的收入。”最终,渠岩抛下一切理论,以村里人的思维方式化解了这场冲击。 在一次次的“白墙事件”中,艺术家出身的渠岩一边做,一边学,他学会了践行米奇尼克的“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只有用“村里的话”才能让村民听得懂,才能与村民达成共识。渠岩和许村形成的平等互惠关系,正是这个艺术乡建项目能够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平衡的建立,也是在艺术乡建过程中他逐渐领悟到的。“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我发现艺术介入现实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必须在社会中构建一个相互的共同体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单项的,要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渠岩说。
渠岩(中间拿图纸者)和许村村民一起进行老宅修复(摄影:常跃生)如何让村里人既能吃上肉,又不受到裹挟,这是渠岩要长期维持的平衡。值得庆幸的是,至今许村既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中的旅游地,也没有变成外来者为主的画家村,许村是许村人的家园,许村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续自己的历史。许村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反而避免了单一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避免了外部过度介入的难题,契合了乡村用自己的方式慢慢苏醒的规律。 青田范式开启新篇章前十年,渠岩在用艺术摸着石头过河,他在太行山中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才是最有效的方案?带着以主体性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以及许村乡建的声誉,他到了青田,此次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这个经济相对发达的乡村,如何沿着主体性这条路继续实施乡建? 相对于许村,青田村的先天条件要好得多。青田是广东的一个普通乡村,常住的大约100户人家。据说青田有500多年历史,全村都姓刘,村里残留着刻有“彭城”两字的石条。彭城是刘邦起家的地方,刘邦的后代都以彭城自证。沿村落环绕的水系完整,“风水塘”坐落村中,聚落形态由“中介巷”展开,主体建筑遵循着《园治》中“先乎取景,妙在朝南”的传统规则,目前村内肌理格局保留完整,绝大多数建筑依然保留传统风貌。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安详紧凑、多彩优美的岭南水乡特色,也让青田得以存留其独有的生活体系。
随处可见的水系成为青田村民最惬意的聚集场所(摄影:王晓红)
2017年9月,渠岩和青田村民一起烧番塔。烧番塔是广东省的佛山、肇庆很多村庄的中秋保留节目。(摄影:谭若芷)2015年12月6日,担任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筑研究所所长一职的渠岩受邀到顺德地区乡村考察,他立刻被这个保留着完整文脉的水乡青田吸引,青田乡建就这样开始了。他表示,相比其它已经商业化和旅游开发的乡村,青田是被现代化遗弃的村庄。由于没有工业,原生态的乡村文明和环境得到了幸免于难,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所以他选择了青田作为试点对象。 这两年中,渠岩将工作重心都放在了青田,并就此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包括邀请专家学者对青田进行调研,完成《村落空间调研报告》,不仅对青田的历史、自然风貌、现状以及周边村落比较做了详细的梳理,还由此制定了乡村建筑改造计划以及新的乡建模式。在他的规划中,乡村和城市应该守望相助,而不是相互矛盾,“青田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典型性,青田的复兴或许可以打造成为全国乡村文明复兴的样本。 《青田大事记》清晰地记录了青田乡建的进展:2016年3月19日,顺德榕树头村居保育慈善基金会在顺德江义古村成立,以此举措积极推动顺德地区的乡村建设;6月,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与杏坛镇政府签署青田乡村建设与文明复兴合作项目书;2017年3月19日,在青田举行的榕树头村居保育慈善基金会成立一周年的庆典上,倡议设立“中国乡村文化活动日”,渠岩提出中国乡村建设新理论,并发布《青田范式:中国乡村复兴的文明路径》;10月20日,杏坛镇举行《青田乡村建设、规划与文明复兴》项目汇报会,渠岩在会上汇报了青田复兴项目书,获得镇政府通过。
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工作坊效果图(设计:郭建华)“如果艺术家、社会介入者不能收敛和克服保守、妄自尊大的态度,不但无法切入到青田社会民众的心灵世界,也无法让艺术家社会介入的初衷落实到当地社会。”这是渠岩艺术介入乡村的经验,在青田的新模式中,他有意隐去“艺术”之痕,发动村镇企业家的力量,以艺术家的“去艺术化”手段,以及“艺术之外”的乡村实践,避免“艺术标签化”“乡村视觉化”和“艺术同质化”的表达,全面深耕乡村在地实践,重新思考社会的构成和人的处境。 与许村相同的是,青田乡建也同样围绕共同体的前提,逐渐恢复乡村文明。“礼失而求诸野”,在礼制沦丧后就要到民间去访求,这句话用来理解“青田范式”特别适用。青田范式就是建立在对青田乡村地方性知识尊重的基础上,思考如何与当今社会连接,共同构建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路径,包括青田村本身所具备的乡村的历史、政治、经济、信仰、礼俗、教育、环境、农作、民艺、审美等方面,建立丰富多彩的“乡村共同体”。九条范式由九个项目组分别开展调研和理论归纳,每个项目组均由当前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著名专家带领,共同深化具有示范意义的“青田范式”。在渠岩看来,与其空喊不绝于耳的“文明复兴”口号,不如通过恢复和接续“地方文脉”、实现对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归,以此解决今日乡村的社会危机与现实困境。
渠岩陪北大社会学教授渠敬东考察青田(摄影:谭若芷)由于长期受到西方艺术思维影响,中国艺术家大多失去了对于中国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关照,等到醒悟为时已晚,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将这种传统消耗殆尽,这种影响已经快速渗透到乡村。渠岩所做的乡建实际上是在保护中国传统文明遗存,反思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危机,以及重建背后的文化逻辑,找回失落的文化主体性。“用艺术的语言,来接续本民族文化的线索,呈现当前社会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提出这些困境的应对之道。”渠岩说。 (本文原刊于《中国艺术》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