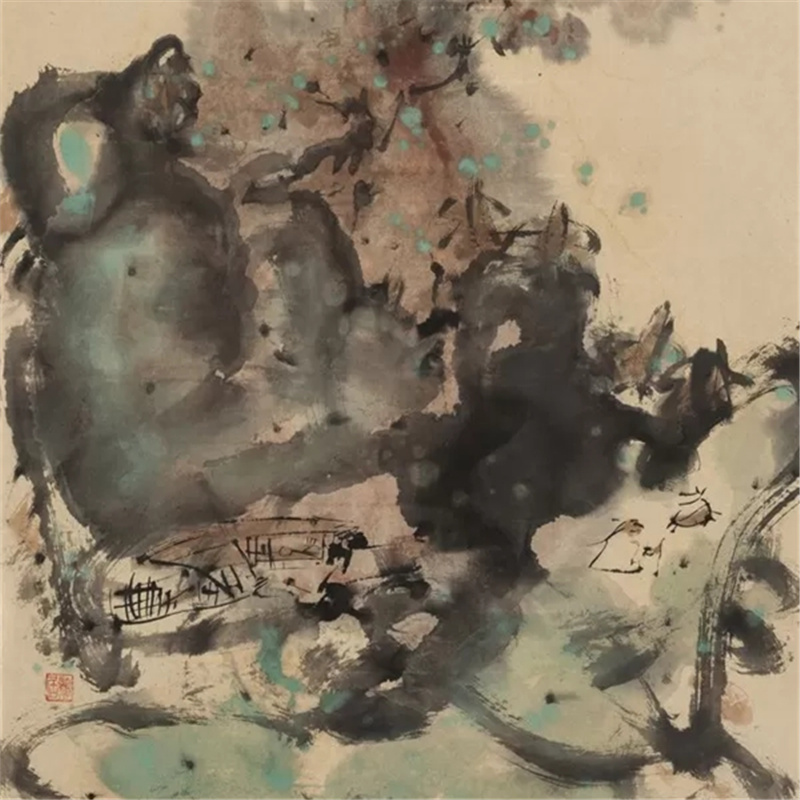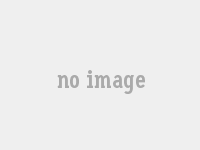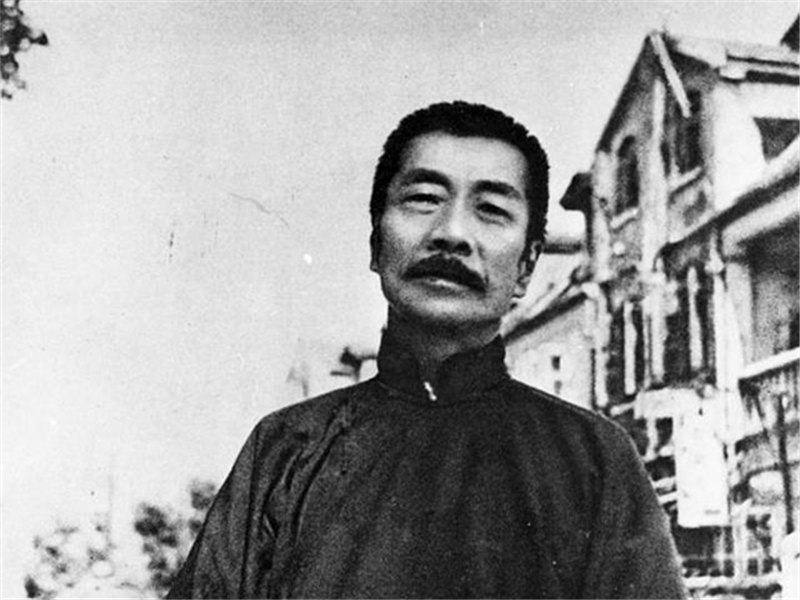对当代作家特别是50后作家进行年谱整理是否必要,关系到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虽然仍有意见认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版图中指认“当代的‘鲁郭茅巴老曹’”,容易混杂其他感情因素,但50后、部分60后重要作家三十多年来的创作实绩,又确实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小传统”。在目前针对新时期文学的多种资料汇编、作家选本与文学史叙述中,关于他们的经典性价值已经形成一套稳定共识,一面为评价其新作甚至理解当下文学生态都提供了有效的历史参照和批评支点,一面又制造着成规。如谈到莫言就一定会从“民间性”“魔幻性”和乡土中国的现代书写等角度入手,余华的研究者都熟悉他的“暴力叙事”与“先锋转向”,论及王安忆就必然涉及“上海书写”等等。这些认识来源于与创作同步的批评累积,由于这些作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关于他们的重要批评往往又关联到新时期文学思潮,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转型的历史意识。这也就带来了必须思考的问题:尚未完成的经典化过程会不会受制于已有的结论?是否应当重审今天“批评”眼光的由来?能否回到历史脉络中,去重识那些被经典化了的作家作品,为理解这些作家还在展开的文学世界提供更多参照?
对经典作家进行年谱整理与研究,恰恰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及年谱体例时,主张“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他还指出:“譬如做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梁启超由此建议年谱编纂者“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但如何对前人批评进行拣选,并以客观呈现谱主事迹为目的编入年谱呢?传统年谱编纂或从文学交往、师友渊源等方面考证批评家与谱主的直接往来与相互促进,或在每年辑录重要的批评观点著述,以此呈现谱主在同时代人眼中的价值定位。针对当代经典作家的年谱整理,如能有意识地以研究现状中普遍认同的观点或问题为参照,既有助于研究者把对当代作家的批评性意见,回收到历史中去;也能把被批评加工过的作家作品,还原到有更多解读空间的发表状态。
年谱整理要将围绕作家作品形成的经典认识,转换成问题,而非梳理脉络的依据。近几年由《东吴学术》杂志组织出版的一系列作家年谱,为作家作品论开辟了重要的史料研究视野。但或许因为“文学年谱”的立意局限,对一些批评认识还缺乏足够的“语境化”,尤其写到在世作家晚近几年的文学活动时,更像是批评资料汇编。一些年谱对构成作家文学实践重要一环的行旅活动呈现不足,年谱中不仅要记录行旅的时间、地点和著述成果,还应借助作家自述等材料尽可能呈现行旅中直接影响到作家身心感觉的事件。
年谱整理借助史料说话,可以有针对性地把一些批评共识落到实处,也要格外注意能形成补充甚至修正的其他材料。对当代作家生平的编年纪事,虽然力求客观,但不能回避对作家创作阶段中某些重要关节点的研究拓展。例如,批评界普遍认为莫言在1984年进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后,以《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持续性的先锋姿态,几年后才开始有“回到民间”的创作转型。李桂玲编撰的《莫言文学年谱》也用翔实的材料,如莫言在军艺学习期间的阅读书目、《透明的红萝卜》的“诞生记”等,在作品周边搭建起了理解这一创作轨迹的多个支点。然而,程光炜教授新近“莫言家世考”系列研究又对这个线索提出了“质疑”。在《高密剪纸和泥塑》中,他引述莫言亡友张世家的一段回忆材料,指出莫言在1986年回乡探亲时就曾专程找高密剪纸世家范作信买了五百余件剪纸作品,这一细节后来还出现在莫言1986年发表的小说《高粱酒》中。当批评家们顺着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潮文学崛起的一般印象,从莫言读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自述中兴奋地发现一个“现代主义者”时,程光炜教授感慨这则材料的发现是“令文学史家难堪的场面”。倒不是说一则材料就能否认此前研究的价值,但确实会迫使研究者去反省,除了军艺学习和西方文学阅读,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莫言?甚至具体考证莫言究竟读了福克纳的哪个译本,他是不是留意到译者李文俊序或其他导读性文字?批评家都注意到莫言此时的创作变化是越来越强调对故乡的回忆和书写,那么能否通过访谈口述等材料收集,落实莫言每年回乡探亲时的见闻?如莫言大哥整理的年谱中就提到,1984年秋莫言四叔被给公社某领导拉货的醉酒司机撞死,连人加牛只赔了3500元,莫言当时给当地领导写了言辞激烈的信。这些琐碎经历在多大意义上构成了莫言创作的资源还有待分析,但针对现成的文学史经典论述可能存在过于清晰和简化的问题,年谱还是要以“并不整齐”的材料去呈现作家创作更丰富、更立体的面貌。
对于当代经典作家的年谱整理,要特别注意如何处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互动。笔者在研究阿城小说《棋王》与寻根文学的关系时发现,阿城在“杭州会议”前后对《棋王》的创作自述,其实发生了一个从强调“知青经验”到回溯“中国文化”的重心转移。“寻根文学”口号的提出,本身就是批评家、作家合力的结果,并将此前已发表的作品追认为寻根意识的主动实践。因此很难把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简单处理成阐释与被阐释关系。有时不同批评思路在历史变动时刻的交锋,能够呈现出作品内涵的多义性;有时作家与批评家,或者带有批评家性质的编辑之间的交流往来,会直接构成作家成长和某部作品出炉的重要环节;有时透过批评家的文章,可以看清作家所处时代的情势。在传统年谱整理的基础上,能不能针对当代作家各自的具体情况,寻找编辑批评材料的新方法,为研究埋下一些可以追踪的暗线呢?
比如不妨把作家自述、作家演讲、作家谈文学艺术的文章,都视作“批评”的组成部分,在传统年谱记载谱主文章目录的基础上,用附录、脚注、索引等形式,标出其中的关键词,提醒读者留意这些观念或表述出现的时间甚至与作家批评史的潜在关联。年谱不必给出结论,但可以呈现问题。例如莫言1998年10月在台北图书馆作《我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讲演,就直接借用了批评家张清华先生的观点,自述从《红高粱家族》至《丰乳肥臀》以民间传奇重述历史的一贯主张。此处如能在脚注中注明张清华相关评论文章的出处,以人物小传形式交代莫言与张清华的交际,并以类似“超链接”的方式提示1984年莫言最初发表《红高粱》时缘起于“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的相关材料,就能自然引人思考莫言对自己历史观的命名是如何逐渐清晰起来的。
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谈到当代文学学科化问题时说,当代文学研究既要向现代文学取法“寻找使之规范和稳定的路子”,又“有许多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切合的途径”。面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争议,年谱研究要以“历史化”的方式,带动对批评诉求中“当代意识”的不断自省。如果说指认经典作家作品,是为了以此为参照丈量当代的人与文,那么年谱学带来的眼光,就是要暂时放下现成的知识与框架,更好地去认识历史中具体生成的人与文。
(作者:杨晓帆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